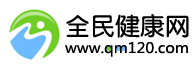禅宗的原理
前面我曾简单勾勒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分析之间的传承关系。我讨论了人的存在以及与之有关的问题;我把幸福安宁的性质定义为对异化与隔离的克服,而其特定方法即贯通无意识,这也是精神分析所尝试达到的目标。我讨论了什么是无意识与意识的本质;在精神分析中,“认知”与“察觉”又意味着什么;最后,我讨论了精神分析者在分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为对精神分析与禅之间关系的讨论作一铺垫,看来我应当对禅宗作一番系统的描绘。幸好这里不需要做这么一种尝试,因为铃木大拙博士在本书各篇讲词(以及他的其他著作中)中,已尽可能在语言所及范围内,向我们传达了禅宗性质的意义。尽管如此,对与精神分析直接相关的一些掸宗原理,我必须作一番说明。
禅的核心是开悟,凡没有体验的人,决不能对禅有充分的了解。由于我没有悟的体验,故只好用一种表面的方式,而不是以应当讨论它的方式去谈论它,即出自充分的体验。但这并非像荣格所说,因为悟“描述一种启蒙的道路与艺术,这在实际上是欧洲人无法去品味的”。就其途径而言,禅并不比赫拉克利特、爱克哈特或海德格尔更使欧洲人难以理解。困难在于获得悟需要巨大的努力;这个努力是绝大多数人所不愿付出的,故即使在日本,开悟者都极为罕见。不过,我虽然不能以什么权威口气来谈禅,却因有幸读到铃木大拙博士的著作,聆听过他的几次讲演,并读了凡能到手的所有关于禅宗的书籍,故对禅的结构至少有一大致的了解。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希望,可以对弹宗与精神分析作一尝试性的比较。
什么是禅的基本目标?用铃木大拙的话来说:“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可以说,禅把蓄积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所有能量完全而自然地释放出来,这些能量在通常环境中受到压抑和扭曲,以致找不到适当的活动渠道……因此,禅的目标乃是使我们免于疯狂或畸形。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由,即把所有蕴藏在我们心中的创造性的与仁慈的冲动都自由发挥出来。我们都具有使我们快乐和互爱的能力,但通常对此却视而不见。”在这段定义中,我们发现禅宗的一些值得强调的基本点:禅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是从奴役到自由的一种道路;它释放我们自然的能量。它防止我们疯狂或畸形;而且它还使我们为快乐与爱而表现我们的天赋。
禅的最终目标是开悟体验。铃木博士在他这些讲演及其他著作中,对此已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说明。我在此要强调的几点,对西方读者、尤其是心理学家,有着特别的重要性。悟不是心灵的变态,不是一种泯灭现实的恍惚状态。它不是可见诸某些宗教现象中的自恋心态。“它无非是完全正常的心灵状态……”正如赵州所说:“禅即平常心。”“无论门朝里开还是向外开,都得靠门枢。”悟对有此体验的人有着特殊的影响。“你的整个心灵现在都将以一种不同的格调活动,这比你以往所经历的任何东西都更使你满足、和平和充满快乐。生活的格调将得到改变。在禅中有着使生命更新的东西。春花更美,山溪更为清澈。”
诚如铃木博士以上所描绘的,开悟显然是幸福安宁的真正实现。如果我们尝试用心理学术语来表达开悟,可以说它是一种人在其中完全和他内外在真实相应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对那真实有着完全的觉察和把握。既不是用他的大脑,也不是用他身上的任何其他部分,而是用全部身心的他去觉察这个真实;不是把这个真实当作一个用思想去捕捉的客体,而就是在那朵花、那只狗、那个人中,在它或他之中,在全部现实性中去觉察这个真实。觉醒的人之所以对世界敞开,并具有回应性,是因为他不再一把自己作为一个物而执着,故变得空灵,能容纳一切。开悟意味着“人的全部身心对真实的充分觉醒”。
开悟不是一种意识的分裂,也不是实际沉睡却自以为清醒的恍惚状态,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当然,西方心理学家倾向于把悟理解为一种主现状态,一种自诱的恍惚状态;即使像荣格这样亲禅宗的心理学家,都未能避免这种错误。荣格写道:“想象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事件,因此,开悟不论是被称为真的或被称为想象的,都无关宏旨。一个已开悟的人、或自以为开悟的人,都相信自己是开悟者’……即使他在说谎,这一谎言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事实。”这当然是荣格对宗教体验的“真实性”一向所持的相对主义态度。与荣格相反,我认为谎言就是谎言,它不是“一种精神上的事实”,也不是其他什么事实。不管荣格的说法有无道理,他这立场决然得不到禅徒们的同意。区分真悟和假悟,对禅宗是极为重要的:真悟所获的新见地是如实的;假悟则可能是歇斯底里或精神病性质的,学禅者会在此情况下自以为开悟,禅师必须使他搞清楚这并非开悟。不让学生把假悟误认为真悟,正是对真实的完全醒悟,用心理学术语来说,意味着达到一种完全的“建设性指向”。这意味着个人不是以接受性的、剥削性的。围积性的或市场性的方式与世界相关,而是以创造性的、主动性的(照斯宾诺莎的含义)方式与世界相关。在完全的建设性状态中,不再有隔开我和“非我”的幕障。客体不再是客体,它不再与我对峙,而是与我同在。我看到的玫瑰不再是我思想中的一个对象,因为当我说“我看到一朵玫瑰”时,我只不过是把玫瑰这一对象放在“玫瑰”这一概念的框架里;而现在我则以“玫瑰即这朵玫瑰本身”的态度来看这朵玫瑰。建设性状态同时就是最高的客观性,我看到的对象不再困我的贪婪与恐惧而受扭曲。我是以对象的本来样子来看这个对象,而不是以我的臧否好恶来看它。在这种领悟方式中,没有幼稚的编曲。它生气盎然,是主客体的浑然统一。我强烈地体验到对象,这对象仍如其本然存在。”我赋予它以生命,它也赋予我以生命。只有那些不曾觉察到他对世界的理解是多么偏曲的失常的人,才会觉得悟是神秘不测的。如果人们觉察到这一点,他也就觉察到另一种可称作完全如实的觉察方式。虽然我们对此可能只有偶尔的体验,仍可想象它是什么样子。初学钢琴的小孩,当然不能如大师一样演奏。但大师的演奏亦不是什么神秘莫测之事,那不过是孩子初始经验的完成。
禅之体验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对真实不扭曲、不抽象化,有两则故事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其中一则是一位禅师同一位僧人的谈话:
(源律师)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
(慧海禅师)曰:“用功。”
曰:“如何用功?’
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
师曰。“不同”
曰:“何故不同?”
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
这一故事几乎不需要什么解释。常人因受不安全感、贪婪和恐惧有驱使,不断地陷入幻象的世界(不一定觉察到这一点),他们给这世界投射以种种本来不具有的特性。上引那段对话固然道出了当时的实际,那么,当今天差不多人人都不是以他自身本具的力量,而是以他的思想去视、听、触、味时,情况是否更是如此呢?
另一则故事同样具有启发意义,一位禅师说:“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于此我们再次看到对实在的新道路。常人有如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人,只看到影像,却误以为就是本质。一旦认识到这个错误,他就知道那不过是影像,而不是本质。但当他开悟后,他就离开洞穴,脱离黑暗而步入光明:在此他看到的是本质,而不是影像。只要他处于黑暗,他就不可能理解光明(如《圣经》所说:“光要照进黑暗,而黑暗不懂得。”)一旦他走出黑暗,他就会明白:以前所见的影像世界与现在所见的真实世界多么不同。
禅旨在认识人自己的本性。它探求“知汝自己”。但这种知识不是现代心理学的“科学”知识,不是那种把认知者自己当作对象来认知的知性知识;禅宗对自我的知识是非知性、非疏离性的,它是知者与被知之物合一的充分体验。如铃木所指出的:“禅的基本思想是达到与人生命内在活动的交融,并以尽可能直接的方法达到这一交融,而不依赖任何外在的或附加的东西。”“这种对人本性的洞察,不是一种外在知性认识,而是一种内在的体验。知性知识与体验性知识的区别,对于禅宗至关重要,同时亦构成西方学者尝试了解禅的基本困难之一。两千年来,西方人(除了像神秘主义派的少数人例外)都相信,对存在问题的最终回答可以用思想给出;宗教与哲学中的“正确答案”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对这种观点的强调,为自然科学的发达铺下了道路。这里,正确的思想寓于方中,并为思想用于实践(亦即技术)所必须,但却不能对存在问题提供一个最终答案。相反,禅则建立在如下前提上:生命的终极答案不能用思想来提供。“在通常的事物发展顺序上,光用‘是’或‘否’的知性方式是相当方便的;但生命的终极问题一旦出现,知性就无法给予满意的回答。”②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开悟体验决不能以知性的方式来传递。“任何解释和论证都不能把开悟体验传递给他人,除非他们事先已具有这个体验。假如悟可由分析的途径而使另一个从未开悟的人完全了解,那么悟也就不成其为悟了。悟假如进入概念领域,也就失去本来面目,从而不再是禅的体验。”
不仅生命的终极答案不能由任何知性体系提供;为了达到开悟,我们还必须排除许多妨碍真正洞察的心智构想。“禅要的是人心的自由无碍,即便是一体大全的观念也是一种威胁精神原初自由的障碍和陷阱。”作为更进一步的结论,为西方心理学家所强调的参与或移情概念,不能为禅宗思想所接受。“参与或移情,是对原初体验的一种知性解释,但就体验本身而言,却不容作任何形式的二元分裂。然而,知性却硬要割裂经验,以便进行知性上的处理,这意味着使经验判然两分。原初的统一感因而消失,让知性以其典型的方式将事实割成碎片。参与或移情乃是知性化的结果,那些没有原初体验的哲学家,则易于沉溺于其中。”
不仅是知性,任何独断性的概念或形相都会限制体验的自发性;因而禅宗“并不认为殚精竭虑地去读经注经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个人的体验,与权威和客观的启示形成强烈的对峙……”禅宗既不坚持,也不否认有神。“禅要求绝对的、甚至脱离神的自由。”它甚至同样要求脱离佛而自由,故禅宗有言:“念佛一声,嗽口三日。”
禅的教育目的,不是像西方那样使逻辑思考日益精密,关于对知性洞察的态度,它的方法“在于把弟子逼入困境,要想逃离这个困境,不是通过逻辑,而是通过更高层次的心灵。”于是,禅师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教师。就他能够把握自己的心灵而言,他是一位大师,从而能把唯一能够传递的东西传递给他的弟子:即他的存在。“尽管禅师能做,他却不帮助弟子把握住这个东西,除非弟子已为此做了充分准备……要把握终极实在,只有通过他自己才能去做。”
禅师对其弟子的态度,常使现代西方读者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拘执于非此即彼的模式:要么是限制对象的自由并剥削之的无理的权威;要么就是取消任何权威的放任。禅代表另一种形式的权威,即合理的权威。禅师并不对弟子发号施令;他对弟子无所要求,甚至也不要求他开悟;学生来去自由,悉听自便。但就弟子愿受教于禅师而言,他必须承认的事实是,禅师是这样一位师父,他知道弟子想要知道的是什么,不想知道的又是什么。对禅师来说,“无需要用言词来解释,也无需发布什么神圣的教条。不论你肯定还是否定,都吃上30棒。既不耽于沉默,也不巧言善辩。”同时,禅师完全没有不合理性的权威,但又明确肯定源于真实体验的无所要求的权威,由此构成禅师的特征。
真正的洞察之完成与性格的转变是密不可分的,除非懂得这一点,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禅。在这一方面,禅宗是植根于佛教思想的,就佛教而言,性格的转变乃是解脱的一个条件。诸如贪婪、自负和自我炫耀等,都必须抛弃。对过去的态度是感恩,对现在的态度是贡献,对未来的态度是责任,以禅的态度生活,“意味着以最大的鉴赏和恭敬心态来对待自己和世界”,这一态度乃是“构成掸宗戒规特色所在的奥德之基础”。它意味着不要浪费自然资源,它意味着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充分使用“你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
就积极的目的而言,禅上的目的是要达到“完全的安全感和无所畏惧”,是要摆脱奴役走向自由。“禅关心的是性格,而不是知性,这意味着禅产生于作为生命第一原则的意志。”
- 2006-11-22什么叫做赔偿性神经症呢?
- 2006-11-22牙科手术之前的心理调适
- 2006-11-22心理门诊的服务内容有哪些
- 2006-11-22哪些人需要求助心理咨询?
- 2006-11-22两个系统之间的交流
- 2006-11-22无意识系统的独到特点
- 2006-11-22无意识一词的不同意义;局部解剖外观
- 2006-11-22无意识概念的合理性
- 2006-11-22神经病——对付现实的工具
- 2006-11-22狂妄的优越感
- 2006-11-22了解个人的生活风格
- 2006-11-22自卑对自我的限制
- 2006-11-22眼泪和抱怨——水性的力量
- 2006-11-22公共场所恐惧症和自杀心态
- 2006-11-22如何识别“自卑情结”
- 2006-11-2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概念中的价值与目标
- 2006-11-22当今精神危机与精神分析的作用
- 2006-11-22解除压抑与开悟(三)
- 2006-11-22解除压抑与开悟(二)
- 2006-11-22解除压抑与开悟(一)
- 2006-11-22禅宗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