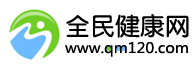解除压抑与开悟(一)
http://www.qm120.com2006-11-22 15:25:10 来源:全民健康网作者:
从我们对精神分析和禅两者关系的讨论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读者想必已经看到,所谓禅宗与精神分析互不相干的看法,只是来源于对两者的肤浅了解。相反,两者的相似之处看来倒更加明显。本章将尽力对这相似之处作一详细说明。
让我们以前引铃木大拙博士关于禅之目标的论述作为开头:“禅本质上是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可以说,禅把蓄积于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所有能量完全而自然地解放出来,这些能量在通常环境中受到压抑和扭曲,以致找不到适当的活动渠道……因此,禅的目标乃是使我们免于疯狂或畸形。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由,即把所有蕴藏在我们心中的创造性的与仁慈的冲动都自由发挥出来。我们都具有使我们快乐和互爱的能力,但通常对此却视而不见。”
对禅的目标所作的这番描绘,可以不加改变地用于描绘精神分析所期望的目标,这就是:对人们自己本性的洞察,达到自由、幸福与爱,释放体内的能量,从疯狂或畸形中解脱出来。
我们正面临着在开悟与疯狂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这种说法也许令人惊异,但在我看来,这却出自显而易见的事实。虽然精神病学关心的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发疯,但真正的问题却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疯狂。设想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他的隔离、孤寂、无能,以及他对这一处境的觉察,人们会觉得这些负担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以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会在这压力之下“崩溃”。大多数人是通过补偿机制,比如使人僵化的常规生活,与群体保持一致,对权力、特权和金钱的追求,在与其他人共同参与宗教仪式时对偶像的依赖,自我牺牲式的苦行生活,以及自恋式的自我膨胀——总之,是以变得畸形而逃避了疯狂这一结果。所有这些补偿机制,都可以使人不致于疯狂,保证他们正常的活动。但要真正克服潜在的疯狂,根本的解决办法乃是对世界具有完全而建设性的回应,其最高形式就是开悟。
在我们进入精神分析与禅的核心问题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些较外围的共同点。
首先要提到的是禅与精神分析相同的指向。克服贪婪是实现禅的目标的一个条件,即要克服对财产、名誉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贪婪(在《旧约》中称为“贪图”);而这正是精神分析的目标。在力比多发展——从口腔式感受,经过口腔式施虐、式感受,到生殖器式感受——的理论中,弗洛伊德含蓄地表述了健康的性格由贪婪、残忍、吝啬的性格发展而来,成为一种积极、自主的指向。用我的术语(仿效弗洛伊德的临床观察),可以更明显地突出这一理论中的有价值因素,即经由剥削性的、囤积性的、市场性的指向,从接受性的指向发展为建设性的指向。不论我们用的是什么术语,精神分析概念中的基本观点就是:贪婪是一种病理现象,它存在于不曾发展出其积极的、建设性的能力的人中间。然而,精神分析和禅在根本上都不是一个体系。禅的目标超越了行为的目标,精神分析亦然。可以说这两个体系都认为,它们目标的实现亦伴随着一种上的转变,即克服贪婪,行施爱与慈悲。它们并不是倾向于以压抑“邪恶”欲望而使人导向一种有德行的生活,而是期望在扩大的意识光焰下,使这邪恶欲望融化消失。但是,不管开悟与转变之间的因果联系如何,认为禅的目标可以与克服贪婪、自炫、愚痴的目标分开,或认为无须达到谦恭、爱与慈悲即可开悟,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认为无须在人的性格中发生上述转变,就可达到精神分析的目的,也是同样的错误。一个已臻建设性层次的人,就不再是一个贪婪的人了,同时也克服了他的自负及全知全能的幻想,从而谦卑地、恰如其分地看待自己。禅与精神分析的目标都超越了,不过,除非发生上的转变,否则它们的目标也是无法实现的。
两大体系的另一相同点,是它们都坚持对任何权威的独立性。这是弗洛伊德批评宗教的主要理由。他认为宗教的本质是虚幻的,是以对神的依赖来取代会帮助人、会惩罚人的父亲的依赖。照弗洛伊德看来,人对神的信仰,是继续他儿童时期的依赖,远非成熟的行为,因为成熟就意味着只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么,对于一个竟然说“提到佛字,赶快漱口”的“宗教”,弗洛伊德有何评论呢?对于一个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任何非理性权威的宗教——其主要目标只是把人从一切依赖中解放出来,使他充满活力,指出只有他才能负起自己命运的责任——弗洛伊德又将有何评论呢?
不过,人们可能会问,这种反权威的态度,岂非同禅师和精神分析者的个人重要性大相抵触么?况且,这个问题指出了禅与精神分析深刻相关的一个要素。在这两个体系中,都需要有一个引导者,他自己已经历过那种体验,又引导患者(学生)去达到那种体验。这是否意味着,学生变得依赖于禅师(或精神分析者),而禅师之言因而变成了学生的金科玉律?的确,精神分析者面临着患者对他这种依赖(移情)的事实,并认识到这一事实所具的有力影响。但精神分析的目的是了解并最后解除这种缚结,把患者带入一个脱离分析者而获得完全自由的境地,因为患者已在自身中体验到原先无意识的东西,并把它归入他的意识之中。禅师——精神分析者同样如此——毕竟知道得多些,故对自己的判断确信不疑,但这绝不意味着他要把他的判断强加于学生。他不曾叫学生来,也不阻拦学生离他而去。如果学生自行找来,要求在其指导下跋涉那通向开悟的崎岖道路,禅师愿意给予指点,但条件只有一个:即学生认识到,虽然禅师很想帮助他,但学生必须自己照管自己。在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拯救另一个人的灵魂。人只能自己救自己。禅师所能做的,只是助产士和登山向导的事。正如一位禅师所说的:“我对你们实在无甚可告,倘若非如此不可,将来徒然贻你们一个笑柄。况且,不管我说什么,终究是我自家的东西,与你们又有何相干?”
对禅师这种态度作出的引人注目而具体人微的说明,可见诸赫里奇论射艺的书。①禅师强调他合理的权威,亦即是说,他虽对射艺懂得多些,坚持学用定规,却并不需要任何凌驾于学生之上的不合理权威,不要学生始终依赖于禅师。相反,一旦学生自己卓然成家,就可以走自己的路,禅师所期望的,不过是能时时知道学生正在做些什么。可以说,禅师爱他的学生。他的爱是一种现实、成熟的爱,是为了学生达到其目标而竭尽全力的爱,然而他又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决不能为学生解决达到其目标的问题。禅师的这种爱是非情绪性的、现实的爱,这种爱接受人类命运的现实,即我们中没有人能拯救他人,但我们又绝不能放弃一切给予帮助的努力,使别人能自己拯救自己。任何爱,若不懂得这种局限,自以为可以“拯救”别人的灵魂,那就仍未摆脱自大与野心的窠臼。
禅师所说的话原则上适用于(或应当适用于)精神分析者,对此几乎无须提出更多的证据。弗洛伊德认为,要使患者离开分析者而独立,比较好莫过于在分析者一方采取镜子式的、客观的态度。但是,像费伦齐(Ferenczi)、沙利文(Sullivan)、我本人和其他一些精神分析者,则重视分析者与患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彼此了解;并完全同意这种联系必须摆脱一切情绪作用和不切实际的偏曲,尤其要摆脱精神分析对患者生活的任何干预(即便是最微细和间接的),甚至也不可要求患者痊愈。如果患者想要痊愈,想要改变,这固然不错,分析者应该予以帮助。如果患者对于改变的抗拒太大,则责任并不在分析者一方。分析者的责任无非是尽力提供其知识与努力,给患者指出应趋的目标。
在分析的态度上,禅宗与精神分析还有一个相同之处。禅的教育方法似乎是要把学生逼入死角。公案①使得学生无法在知性思维中寻求庇护;公案就像一个障壁,使学生不能再逃避。精神分析者也做着(或应当做着)类似之事。他必须避免给患者以种种解释和说明的错误,因为这只能妨碍患者从思维跃入体验。相反,他必须把合理化的藉口一个个排除,把拐杖一个个撤掉,使患者无法再逃,使他突破充斥心中的种种幻象,从而体验到真实——即意识到以前未曾意识到的东西。这一过程常导致大量的焦虑,若不是分析者排除这种压力,这种焦虑有时会阻碍对虚幻物的突破。但是,这种排除,只是因为分析者“在那里”,并不是因为言词,言词只能导致阻止患者去体验只有他才能体验的东西。
我们迄今所讨论的,都是禅宗与精神分析之间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是,除非我们公正地把禅的主旨(悟)与精神分析的主旨(克服压抑,把无意识转变为意识)进行比较。否则这种比较是不会令人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