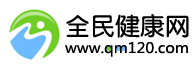半生的遇见
http://www.qm120.com2007-07-17 15:46:55 来源:全民健康网作者:
(1) 家在朱围子屯
引子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经历,我的经历,很简单:换了两个职业:教师、公务员,没离国家干部;搬了三次家,从朱家围子到王大院,再到政府所在地,没离灯塔乡;在家获得四种“职称”:爷爷、儿子、父亲、丈夫,没离开责任;单位主管五项工作:农业、政法、信访、合作经济、给书记乡长写材料,没离开服务。
此书,写我自己的事;语句的结构,像面对面唠嗑,无拘无束;决不絮叨,能一句表述则不再二,像漫画,抓住特征。
我遇见的人,都是好人。只是性格各异。我力求写出那个时代、那个时期、那个时候的历史对我的影响。我不影射谁,不攻击谁,不辱骂谁。我只写我的坎坷经历,我得意过、风光过、也落魄过,栽过跟头。我对他们 的评价尽可能调好焦距,背景虚些,特点突出。
我叙述的人原来大都是真名实姓的,欲保持原有滋味。现在则虚构姓名,以免惹来麻烦。“本篇故事纯属虚构”,只限于在评价时便于展开。凡属类似情况,劝君千万莫对号,对号准确,法律后果自负。
半生遇见之一 家在朱围子屯
1.母亲、启蒙老师
我是个娇孩儿。妈妈在30岁那年冬月十五正晌午时生下我。妈妈曾生过一个儿子,没活半年就夭折了。长的俊,据说让过路的小鬼给领走了。所以母亲对我格外呵护。妈妈六年后生了我,格外小心,成天叨叨着叫我“丑八怪”,这样,过路鬼就不惹了。别说还真灵,我活到现在还好好的。实际上我的乳名叫“盘脐子”,是我的继祖母接的生,落地时脐带缠脖子,瞎奶奶就说叫“盘脐子”吧。
我的生日是公历1958年的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因为生长在大跃进年代,大舅说:“大名就叫孙跃旗吧”
母亲担任村的妇女主任,在我两岁那年,抱着我参加县里的会议,正赶上一帮小孩出水痘,吓得妈妈会没开完就回来了,从那天起,就再没有上班。
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是个小个子的小老头名叫孙明星,很近视,下课的工夫,他一边抓虱子,(那时的虱子不知咋那么多),一边给我们讲故事。记得有一次,他讲得津津有味,讲完后自己笑出眼泪来。可我们没一个同学乐。
“有一个男老师,身上的虱子特别多。一天,他抓虱子的时候,捏着一个虱子问学生:你们知道这虱子是从哪里来得吗?学生们都象拨浪鼓似的摇头,齐声喊:不知道。老师问:你们想不想知道啊?小学生齐声喊,想。这个老师小声告诉,这个虱子是你爸爸身上的,后来爬到你妈身上,再后来爬到了老师身上。哈哈哈哈!”
我们大眼瞪小眼,心想:老师笑啥啊。
二年级的老师更有趣。我们叫他钱老师,他的哥哥在公社当副主任,算借光。教我们识字,总把标准音念错,偏偏我又叫真,举手,站起,指着黑板上的“中国”发言:“老师那字不念zong 念zhong 、guo 不念三声,念二声”然后,钱老师就在黑板的右上角特意腾出一块来,写道:孙跃旗在课堂不注意听讲。我也是,挑起来没完没了,钱老师又堂堂课出错。
钱老师家访了,对我妈妈说,你得给孩子看看,好象学过力了,学出病了。
好象不到一学期,文教组听到群众反映来听课。就让钱老师到总点的校办猪场喂猪去了。
我七岁念书,生日小,确实不懂事。小学的一、二年都在朦胧中度过。我常画小人,用蜡笔画,小朋友看好玩,朝我要,我就让他们用2张纸来换我的画,后来用一本换一幅画。
他们确实羡慕我。我的家庭条件在全公社也数前三名。我的父亲30岁那年,从我的叔伯大嫂那学会了裁缝,使家庭的收入在当时是高水平的,常看见爸爸妈妈挑灯夜战,缝羊皮袄,一件18分。爸爸排行老五,是爷爷最小的儿子,娇生惯养比我厉害,20几岁的时候,曾学习照相,因为天天早起给师傅倒尿盆,吃不了苦,吵着闹着谎称怕学照相总睁一眼闭一眼的再弄个斜眼。照相没成,做买卖又陪,只好呆着。我业余爱好照相是不是遗传啊。
2.地主子弟和刘老七
我们屯唯一的大地主,姓朱,屯子名就是他们家立的。老地主早在土改时就正法了。据说是恋着小老婆没回江南,吉林的扎兰湖旁,电视剧《圣水湖畔》跟前。那里的地多,但是,如果回吉林他排不上大地主,也就不能被革命。是我母亲的干爹。镇压前,母亲曾透风给干爹,让他快逃命。老地主舍不得心上人,结果被结果了。他毙的第三天,上面来了精神,不让镇压了,可惜啊。爱江山更爱美人。
南乡有个土改干部,毕乡长,大老粗,掌握生杀大权。秘书请示工作,“这个地主处理吗?”他说:“处理”秘书是问的毙,他以为是关押,错杀了。
从小爱看小人书,小人书净写、画大地主多坏,我的脑海里的地主形象坏透了。朱大地主的儿子属于地主子弟,我也恨他们。因为我缘故,应该叫他大舅,可我的阶级感情观念深,从来不叫,而且还严厉反对母亲到他家串门,他家在我家房后,中间隔个道。有一天,天色刚黑,月色淡淡,我召集尹小子和荣二,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用土块当,对朱家一顿猛轰。我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在井沿旁的大墙上,把我们三个的身体轮廓用粉笔描下来,下面注解:是我,是我,就是我,砸的就是地主窝。妈妈后来知道了,把我说了一顿,朱家不以为言,双手一拍,哈哈大笑:“这盘脐子,看书看的,把我们当恶霸大地主了”
我的淘气,是有艺术的,我和尹小子、荣二直捣地主家的事是刘老七告的秘,我们三人行动小组决定夜袭刘老七家报复。我们准备了长竿和大马针,尹小子持手电,大约晚8点,我们摸黑到刘家的房子东,荣二拿着长竿照房檐的鸽子窝捅去,由于忙,鸽子惊飞了,屋里有个声音“谁啊!”我们吓的撒腿就跑,我告诉他俩兵分三路。
鸽子没捅着。我们不甘心,次日又去了,尹小子刚把电筒的光照到鸽子窝,就听见黑影里来了一声吼;“好家伙,逮着你们了!”
我惊呼道“快尥!”
我们跑散了,我心里琢磨,刘老七在黑影里看清我们的面孔了,咋办?我灵机一动,回家换了一套衣服,就若无其事的样子,溜达到生产队,那里的人不少,我刚去,听见背后喊我:“盘脐子,你以为换衣服我就不认得你了”
那么多的人,把我羞的无地自容。我在朱围子屯是个以仁义评价的,这件事让我蔫了些日子。朱围子屯就我没外号,全屯一多半的人有外号,刘老七的家族都愿说,人们起外号“刘七叨叨”还有杜二扁、隋大矬子、尹瘸子、梅大尖、荣二坏、赵巡案、孙大鬼、周干巴、张秃子都有讲
3.会接生的瞎奶奶
我的奶奶是爷爷在做生意的道上拣来的。爷爷念牛马经,外号“孙老客”据说他的眼睛毒,牛、马,他一搭眼就知道口(几岁),他的牛马经让我的叔伯五哥“孙大鬼”遗传了。和爷爷一起从山东登州府逃荒来的还有申洋的爷爷、荣二的爷爷。
不只为什么,奶奶反对我和申家、和荣家孩子交往,我不知为了啥。奶奶说:“申洋的爷爷和荣嘉鑫的爷爷都是做买卖的,坏透了。”
我没听奶奶的话,仍然找申洋和嘉鑫玩。我和申洋和荣嘉鑫是好朋友。
奶奶有俩女儿,在哈尔滨平房区的,我们叫“二姑”、兰西县的红旗乡的,我们叫三姑。我十岁那年见过两姑姑。
奶奶是睁眼瞎,高个子、瘦削,我和弟弟都是她哄大的,用背驮着我。好温暖啊,领我走东家、串西家,5岁的时候,我知道奶奶眼睛看不见东西,我躲在水缸空藏起来不出声,奶奶以为我丢了,沙哑地喊:“盘脐!盘脐!”。我得意地笑了,“咯咯”扑向奶奶。
奶奶虽然不是亲奶奶,可是我们家人,爸爸、妈妈、我和弟弟都从来不嫌弃。记得9岁那年,我的小我一岁的表侄子(舅舅的孙子)骂我一声奶奶,让我把他的脸蛋扇肿老高。
奶奶会接生,她就凭触觉。我至今还能回想起奶奶的那双大手,柔软的大手。我们屯30多小孩都是他接生的,连我和弟弟、还有荣嘉鑫--。你说怪不,这30多小孩都出息人了,我是比较次的,还是副科级呢?荣嘉鑫是副厅,在铁道部一个集团公司当党委副书记。
爷爷死的早,我没见过,奶奶一直在我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接生一个赏钱5块,经常给我买糖块吃。长大了见糖就烦。我的糖尿病和这有没有关系,我没问过大夫。
突然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爸爸、妈妈吧嗒吧嗒掉眼泪,奶奶一边拉着我,一手扯着弟弟,哭着说:“俩儿孙子,奶舍不得你们哪!”奶奶就在全家的哭送中,上兰西的三姑家了。一直没回来,成了永别。
4 矮个子外祖父
外祖父,矮矮的个子,像列宁。
他的命苦。外祖父31岁那年,舅舅遇到了马车祸,他家是大人家,种地时,马毛了,舅舅被马踩在蹄下,伤了膀胱,就没起来。
舅舅的死给外祖父的打击犹如晴天霹雳。舅舅有才,写一笔好字,而且聪明。我曾珍藏他的手稿,可惜88年搬家时丢失了。别人赌,舅舅爬墙豁,玩的排九,看准了那门,压上,嘿,赢了,十回有九回赢。不恋战,就走。人称:李二秀才。逢年过节,左邻右舌都找舅舅写春联。这一点我随姥姥家人。让外祖父操心的是,二才过门没满月就摊上恶事,二死活不走,非得伺候姥姥一辈子,那是解放前,没办法,让大舅(我大姥姥的儿子)续弦作了二妻,但是孩子随外祖父,归这支。
五十年代初,颁布《婚姻法》,大舅让村领导找去,回来阴沉脸,跟二说:“你走吧,新社会,一夫一妻”. 二死活不肯,大舅把她的行李全扔出去了,二自己检回来。又扔出去,又拣回来。面对这无奈,外祖父做主了:“就别逼了,我找领导说说”我的四大伯是生产队长,对这样私不举官不纠的事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现在想是亲戚的作用。
外祖父命苦,晚年丧子,中年丧偶。但是还算幸福的妈妈和姨妈对他孝顺,他的侄子不次于儿子,甚至强于。外祖父和他的两个哥哥都长寿,都超80岁,外祖父是1979年去世,享年84岁,那年我儿子才刚满2岁,他非要在开光的时候看他的太姥姥,平时有好吃的也送到太姥姥嘴。家庭影响啊!第二年外祖父祭日,我在县城念师范,没回家,我写了一篇祭文,趁烧了,寄托哀思。
祭文片段摘录:
“冥冥中的外祖父,余乃贵外孙,今师范就读,效舅父才气,袭孙氏家风,不辱使命,当肯学以丰羽,改制以求长。寥寥几语,愿我的泪水化作雨、思念化作风,飞吧,飞到冥城,捎去外孙的崇敬。”
都说矮个子寿命长,我的母亲79岁了,也是矮子,身体健康,满面红光,好象60多岁的人。我看她老人家再活10年没问题。
5.阴天脸的大舅
我小时侯最怕两个人,一个是大舅,另一个是四大伯。他俩的共同点是从来见不着笑脸。我想是他们太操心吧。大 舅真操心啊,他是操心累死的,死那年才57岁,在公社当食堂管理员。大家庭23口,三个老人,两个妻子,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妹妹、女儿。如何轮饭班、伙食标准,样样过问。全乡就他家是大人家,五间房、四代同堂。可惜,在生产队解体的第二年,也就是大舅死后第二年,大家庭瓦解了。
长辈都说我托生差了,我该是女孩。说我的性格,特像女孩,因为愿意做一些女孩的事儿。12岁的**和我的表姐表妹做在热炕上织袜子、刺花。我们有说有笑,表姐小蚱子脸一白:“我爸回来了”立刻,笑声烟消云散,一个个避猫鼠似的。
我呢,依偎在炕角,斜视着大舅阴天脸。
“一个小子家,织什么,钩什么啊!打折你的腿” 大舅说话时扳着面孔。
吓的我蔫蔫地溜了。大舅的白眼仁实际不多,但他好白我们。
这是假象。当公社的管理员,有特权。时常带些好东西回来,自然要分给三位外祖父、两窝孩子、孙子孙女,我呢也有一份。他把光头饼干递给我的时候,我也不敢正面瞅他,他笑的样子,一种酸苦的笑。好怕人啊!
我结婚时才19岁,秘书不给办登记,大舅找的秘书给办了。
大舅正直,据说他对公社的主管领导,很生气。那位领导好吃,大舅仔细,自然舍不得,无奈人家是领导,只能生闷气。生气作病,大舅得了肝癌,一个月就瘦的一把骨头了,白眼仁更多了,脸更阴沉,更长了。可怕极了。
这是我出生后第一次知道“癌症”这个可怕的字眼。大舅被折磨得嗷嗷直叫。
大舅的死,扔下了年迈的外祖父,妈妈说,大舅不死,姥爷不会走那么早。还扔下了两个和一个13岁的表弟大山(和二生的)从此李大家,人心散了,没了主心骨,日子难啊!
大舅临死前,告诉妈妈,“盘脐子太懂事,小心惹祸啊!”
6. 支委四大伯
我不迷信。可我们家接二连三的事让我犯嘀咕:两个舅舅英年早逝、我的三大伯也是刚结婚骑马掉井里摔死了、二大伯是马倌骑马摔得脖腔骨缩进去了、四大伯上甸子拉草站在草车上马车毛了,四大伯摔下来,高位截瘫一个月就见马克思了。
别人的研究结论:我爷爷是念牛马经的,杀牛杀马找晚下辈了。这不都出在马上。你信吗?
四大伯参加过抗美援朝,挂过彩。生产队长、还是大队支委。他认真,人称孙老狠。50多岁的人,满脸褶子,抬头纹沟能放进筷子。
在家庭他权威人物,打过仗,地方官,又主持正义,所以朱围子屯我们三家的大事小情都和他商量。
他是功臣,打四平,血流成河啊,别人听到冲锋号,像弹簧一样喊着往前跑,四大伯稳,冲锋号一响,他数数:1、2、3、4再冲,为啥?敌人换的空,如果四大伯是司令员,肯定死不了那么多战士。
我说过,除了大舅,我怕的第二个人就是四大伯。他冷面,长的黑瘦。生产队开会,他讲话:“这个,这个,”没完,他讲的啥事我不记得,那时才8岁啊,我管他讲啥。就像给钱老师挑错别字一样,我在四大伯讲话的时候,板着手指数“一个这个”“两个这个”一共39个,有一次,我边数边说,让四大伯发现了,没骂,眼睛一瞪,吓的我屁滚尿流。
我家前面是小学校,淘气的我和惹祸的尹小子,为了看学校屋里的小人书,把窗户玻璃敲碎了,正巧被四大伯撞见,一顿臭训:“盘脐子,不懂事呢,这个,这个,你也是学生,这个,这个,损坏东西要赔。回去”
我撒腿就跑,后面又喊“回去拿钱!”
我爸爸是老疙瘩,自然吃香。耍钱输个精光,是四大伯从兰西的二姑家领回来的,差点死。79年人们还没养奶牛,可四大伯近水楼台,从肇东的宣化牵回2头带犊的奶牛,家庭一下子富裕了。
不但我敬佩他,生产队的老百姓都服他,他给他们争口袋。生产队大帮哄的时候,我们屯分红在全乡排在第二名。
四大伯死那年,我已经当了教师,守灵时,自然少不了我。公社来人通知,次日公社来领导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四娘翻箱倒柜找四大伯的照片,没有。只有抗美援朝时佩戴军功章的照片。
四娘说:“跃旗,你画一张像吧!”
我回家取来了绘画碳素笔,照着那张佩戴军功章的照片画了小半夜。
遗像有八开纸大。次日,公社领导没来,据说是四大伯不够级。那张遗像自然也没用上,家族的人、屯子里的乡亲把他掩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