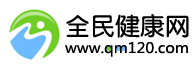中国20万“渐冻人”:目睹自己死亡全过程(图)

除去亲人,还有保姆三妹(左)与张红相依为命,“她用陕南人的温润质朴,陪伴着遍体鳞伤的我,周到地照顾着我的生活。”(张红语)
渐冻人
如果你像他们那样每天看着自己滑向无法抗拒的死亡你会怎样?
在中国,有20万“渐冻人”,实际上可能更多。
这是一种恶性病,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得病的人像被冰雪冻住一样,丧失任何行动能力,但这个过程不是迅速的,而是身体一部分、一部分地萎缩和无力。
今天是腿,明天是手臂,后天到了手指,连控制眼球转动的微少肌肉也不例外。最终等待他们的是呼吸衰竭。
不过,这一切都在他们神志清醒、思维清晰的情况下发生,他们清晰地逼视着自己逐渐死亡的全过程。
渐冻人症是运动神经元疾病的一种,学名叫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简称ALS),又因美国著名棒球明星Luo Gehrig此病而称为葛雷克氏症。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崔丽英说,该病发病率为十万分之四,多发生在40岁以后,中国约有20万患者。
近6年,在北京组织“融化渐冻的心”登记的3000例渐冻人中,浙江省有100例。
目前人类对于此病知之甚少。既查不到任何发病原因,也没有办法治疗,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只有3年。
得这种病最有名的要算英国人霍金,可惜这个科学家可以掌握宇宙起源的奥秘,但不能阻止生命的力量一点点从他的身躯消失。
请原谅我一开始就描述渐进死亡这样残酷的片段,但采访前查阅了很多资料的我问自己,当生命被冰冻住,我会有勇气吗?如果我得了这种病,我每天会干什么?
采访一周后,我发现,他们的乐观足以让人们重新去审视生命的本质和意义。
他们直面死亡逐渐来临的过程,先是悲痛,再是愤怒,继而无奈,最终平静。
逼视自己的死亡,这是怎样的残酷,怎样的顽强!
看着软弱无力的他们,我们分明看到生命发出高贵的光芒。
文/汪再兴 摄/贾代腾飞

这套从国外带回来的软件,让张红有了和外界沟通的可能。她现在每分钟能点出五六个字。
爱像死亡 因为结局令人无法抗拒
张红:监狱里的孩子叫她妈妈
“姐,你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眉毛是绣过的?”我问。
张红努力地抽动了下面部的肌肉。
一边的保姆补充说,她的意思是,是的。
上周六,长发被剪掉的张红坐在电脑面前,全身如同被坚冰冻住,动弹不得,一旁的保姆在喂她药吃。
只见张红将嘴巴张大,保姆如投飞镖一样迅速将药片投入到她的咽喉深处。然后,张红用尚未失灵的喉头肌肉吞咽下去。
张红是一个渐冻人,47岁。
发病前她能一口气登顶华山
9年前的张红,在杭州西湖柳浪闻莺拍照。化妆后的她挺起丰满的胸脯,两只手不停尝试着摆不同的姿势,直到摄影师叫了不要动,才歇息下来。
如今,这张照片是她的电脑桌面。
2010年10月18日下午,陕西省西安市天润园小区3楼,保姆三妹像扛大米一样,将张红从电脑桌前扛起,然后放到沙发上。
张红一动不动躺在沙发上,用呼吸机强制吸氧,她几乎丧失全部行动能力,不能翻身,不能言语,只会在喉头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
秋天的西安,阳光很好,一束追光打在张红的蓝色氧气面罩上,惨蓝的色调。这是一天中,张红少有的歇息时光。
5年前的张红喜欢旅游。一张在珠海海滩的照片上,她穿着泳装惬意地趴在沙滩上晒太阳,青春照人。
华山、黄山、庐山,几乎中国所有的名山,她都能一口气登顶。登顶后,她喜欢坐在最奇峻的岩石上拍照,背后青松独立。“你很上照。”拍照的人说。
正如照片所显示的,没生病前的张红一直很自信。
2001年,张红辞职想去北京创业,走的原因跟当时多数待在国企的年轻人一样,出去闯闯。另外,她在北京出生,回到出生地是她的梦想。
“如果你辞职就不要回家了。”张红的妈妈郑宝珍说。
两年中,她真的很少回家,最后一个岗位是在北京高科技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在北京买了房子,买了车。
后来,郑宝珍觉得,女儿喜欢就随她去吧,和丈夫张焕录到北京照顾张红。

台湾渐冻人陈宏,在他人帮助下,眨眼写出七本书。平均每拼出一个中文字,要眨8到10次眼睛。 资料图片
两级台阶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最先发现闺女走路有问题,是去超市的时候。我看她右腿有点瘸,一瘸一拐的。”郑宝珍对丈夫张焕录说。
张红的博客记录下身体从有力到无力的过程。
“2005年五一长假,我到香山饭店小住。每天早晚揣着2块钱爬香山,40分钟登顶,一根水果冰棍奖励自己。其他时间则坐在花园里看书。到了6月份,就开始无缘无故地摔跤。走路时,右脚像不是我的一样,根本不跟着我走。然后是上下台阶困难,尤其是下楼梯,我已经记不清摔了多少跤。我家单元门外有两级没有栏杆的台阶,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有时候我要站很长时间,才能等到过路人扶我一把,否则几乎每天都是摔着下来。”
“我尽力要去走,但总是摔跤,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张红写道。
医生只能开出安慰药
之后,张红和所有的求医者一样,身心俱疲。
“我看了北医三院、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宣武医院、西京医院、湘雅医院,从运动医学到骨科、神经内科到神经外科,做了7次核磁共振,经过两次专家会诊,前前后后二十多位专家教授,说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病名。”
2005年秋天,父母陪张红到北京协和医院做最后的诊断。肌电图完成后,医生给出了一个确定的答案——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
随后,张红走到医院的走廊给同事打电话。父亲张焕录小心翼翼地问医生:“好治吗?这病。”
“没治。”医生低着头说,“开点安慰药吧。”
“什么叫安慰药?”张焕录问。医生说:“就是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吃了也没用,最近闺女想吃啥,就给她吃啥吧,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一旁的郑宝珍哭了。
如果我不在了,你们怎么办?
张红的一篇博文开篇说:“确诊后我终于可以死个明白!”
确诊当天,张红送父母回家,然后去单位上班,再回家。
家中无人提及病情。夜晚,张红走进父母房间对父母说:“如果我不在了,你们怎么办?”
母亲揽住张红的头说:“你不能,妈妈不会让你死的。”
父亲站在黯淡的灯光下,悲痛地说:“这不是要了你爸爸的命吗?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失去你,我和你妈妈将永远生活在痛苦中。”
全家哭成一片。
父亲俯下身拍了拍张红的头,慢慢地走出去,屋里只有母亲郑宝珍抽搐的声音。
每夜厉声惨叫全身抽搐
“尽力地去走,使不上力。摔倒后,站起来强拧着走,自己开车去吸高压氧,做治疗。”
张红在电脑面前打字对我说,那时,她心存幻想。
确诊后,张红还一直在单位上班,直到2006年4月,莫名其妙地一跤摔下去,半天没能爬起来,让她意识到:再坚持上班,就成累赘了。
2007年春节,张红回到西安,和父母住在一起。家里四处安装扶手,张红希望通过在扶手上锻炼,延缓身体力量的丢失。
那一年,郑宝珍夜里根本无法入睡。
“得这种病,人是清醒的,但眼见自己身体一点点地丧失行动力。”2010年10月18日晚,郑宝珍歪着头靠在一张椅子上,曾经做过医生的她说,从没见过这么残酷的病。
每天夜晚,张红卧室中传出厉声惨叫。
“全身抽搐,小腿,大腿,全身都抽。”一滴泪水淌过老人的脸颊,“我无法替她去疼。”
一个晚上的折腾后,张红全身湿透。疲倦的郑宝珍走出门去,刚好邻居也出门,郑宝珍问邻居:“晚上吵到你们了?”
“没有啊,昨天我睡得可好了。”邻居笑笑说。郑宝珍说,邻居都是好人。
“强烈抽搐之后,身体的力量犹如被上帝收走一般丢失,你无法挽回,你也无力挽回。”一个同样得病的病友在网上总结道。
张红在日记中记录:2007年初,四肢无力,双腿僵直痉挛,拉着能走,说话断续无力;2008年年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能连续讲3-5个字,拉着扶手能站30分钟,舌肌无力。
郑宝珍发现,女儿把“你骗我”,说成了“你便我”。

对没有力气抬起手腕的桐乡渐冻人沈晓阳来说,上网聊天是很困难的事,但也是不多的乐趣之一。 黄陈锋 摄
连指尖敲击鼠标的力气都没有了
不可逆转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尽管曾有过幻想。
2008年末,张红已经完全不能说话,不能站立,咀嚼、吞咽开始出现问题。
那个时候,郑宝珍也没有适应女儿的变化。“你说能怎么办?她脑子清醒,但是不能用手,不能用嘴巴,着急的时候,她只能乱喊乱叫。”
女儿愤怒,拼尽全力从喉管里哼出声音,但郑宝珍听不懂。
女儿就用白板书写狂草,后来连狂草都写不出来了,怎么办?“只好歇斯底里地哭”。
上周六上午12点钟,张红起床,保姆三妹扶她穿衣,察觉有异,她立刻将张红背到马桶上,褪下裤子,一阵窸窣。
之后,三妹将张红抱到电脑桌前,先用绳子从张红的腋下穿过,死死地将她身体固定在座椅背后。“这样她的身体就不会左右移动。”
然后,三妹用两块垫子架起张红的胳膊,把她的手放在电脑鼠标上。左手推右手,她移动鼠标。
“现在连指尖敲击鼠标的力气都没有了。”张红的丈夫说,唯有靠一种特殊软件,只要鼠标在屏幕上停留0.5秒,就能自动点击或打开窗口。
煮饭烧菜要一个上午
80岁的郑宝珍说,以前自己不会做菜,现在女儿生病了,没办法只好自己做。
老人因为女儿学着做菜。每天早早起床,挪着小碎步,在厨房里忙碌。
“我都不知道怎么给女儿做饭,她咬的力气几乎没有。”土豆被煮成糊糊,高压锅里的里脊肉也要煮到最烂,常人一个小时做的菜,老人做了一个上午。
中午,张红吃饭。母亲用一上午,做了3道菜:土豆炖胡萝卜、黄瓜炖肉、浇汤豆腐。
三妹一口一口喂张红吃。土豆泥顺着口水从嘴角流出,三妹赶紧擦拭。
下午4点,郑宝珍拄着拐杖,照例去菜市场买菜。她的腿脚已经很不利索了,下一个坎时,84岁丈夫张焕录赶紧用手搭着她:“慢点下。”
家里的冰柜存着螃蟹。怎么给张红吃?老人将螃蟹腿砸开,一点点地把肉剔除出来。一个上午可以弄出一小碗。
给监狱里的孩子写信
生病后的张红开了个博客,叫“我想对你们说”。
她实际上写的是死亡日记,记录下每天生活的点滴。张红说,她想写,特别想写,想让外人知道这种病的痛苦。
只有在网络上,她的内心世界才能被人知道。每天800字,张红日积月累地写了9万字左右。
除了写日记,她上午定时会打开QQ,等她的干儿子,一个刚刚从监狱走出来的年轻人。她希望帮助这些犯过错的孩子找回生活的信心。
闲暇的时光,张红给这些在监狱的孩子写信,鼓励他们。
监狱的孩子也不断回信。一个孩子在信中说:“看到妈妈如此坚强,我才知道我的人生应该有新的开始。”
回信堆满了一大盒子,放在张红的脚边。三妹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看吧,中午都看不完,看不完信就别吃饭了。”
我笑。
常问自己爱是什么
一天大梦初醒,张红敲下这样一段文字:
“那些日子,除去亲人,还有一个陪护(三妹)与我相依为命,她用陕南人的温润质朴,陪伴着遍体鳞伤的我,周到地照顾着我的生活。”
常常问自己:“爱是什么?”
“爱像死亡,因为结局令人无法抗拒。这是我听到的最为震撼的回答,感同身受。”
一个读者在她的博客上回复:“虽然我们的生命很脆弱,但是我们的意志可以是坚强的。在你的身上我看见,面对苦难原来也可以如此从容。”
她看后笑了笑,继续打字。
这是张红得病后的第6个年头,2010年10月19日,星期二的一个下午。
特派记者 汪再兴 摄影 贾代腾飞 发自西安

张红喜欢杭州,患渐冻人症前,每年都会到杭州品尝明前茶。这是她最后一次到杭州,在西湖边拍的照片。
下一个离世的人,会不会是自己?
渐冻人聊天群:每年20个头像熄灭
特派记者 汪再兴 发自北京
聊天群号56815281,截止到10月17日,里面159人。
群名:渐冻人关爱俱乐部。
我问群主陈霜,为什么要起一个叫“俱乐部”的名字?
他说,怕死,哦,不,是怕提到死。
由于,渐冻人(ALS)这种病惨烈,这个群一年平均会死掉病友20个。
每当群里有一个人退群,或者头像许久没有亮起,剩余的人在哀悼片刻后陷入集体的沉默。他们在想,下一个离开的人,会不会是自己?
同为渐冻人的陈霜说,也许三五年后的某一天,群中所有头像都不再亮起,或者就剩下一个人,面对大片的空白……
他喜欢天天在网上回答问题
群里的人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的身体能力,不能在现实中行走,不能说话,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思考,所以他们依赖网络,网络让渐冻人的肢体有所延展。
2010年10月21日下午,一个网友闯入群里说:“我妈妈又哭又笑的,怎么办?”
群友说,要是你这样去逼视渐渐死亡,你也会又哭又笑。
渐冻人张红也在这个群里,她在博客中写群里的病友:“每个患者背后都有一个无奈的故事,就算有一天他们会离开,但至少在巨大压力下,他们为生命奋斗过。面对同样的命运,他们学会从容、团结和尊重。”
网络让他们抱团,互相取暖,让他们觉得,现实中无力的事情,在网络上都能做到。
一个群友告诉我,他就喜欢在百度“知道”上等人提问,“有人一提问,我就帮着他在网上找资料,我回答上了,我会很开心。”
一天他可以回答几十个问题,“这样我至少可以保持着生的尊严,我还有用。”
这一别,谁也未想到竟是永别
建群至今7个月,群里和陈霜关系比较好的3个病友相继离世。“你能够想象得出么?一个人前几天还在群里嚷着看世界杯开幕式,等到小组赛刚开始,他的头像就永远暗下去了。”
病友“寒冰”就是其中一个。她最后一次上线说:“我姨妈今早6点走了。也许真的只有走了才是一种解脱。”
“寒冰”的姨妈也是渐冻人。当陈霜还来不及安慰“寒冰”,“寒冰”头像就暗掉了。
这一别,谁也未想到竟是永别。
天天上网的“寒冰”已经连续几天不上网了,群里的群友都说,寒冰阿姨到哪里去了?
直到有一天,“寒冰”儿子用“寒冰”的聊天号对陈霜说,因为后期护理不到位,妈妈在今年9月12日仓促离世。
不久,陈霜在QQ空间里贴出悼文:“寒冰阿姨放弃了一切曾经努力追求的东西,永远离开了我们。”
绝望后便是人与人的不信任
2010年10月21日上午,北京东直门的小办公楼内。中国医师协会、“融化渐冻的心”社会公益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高红一如往常,在接听患者打来的电话。
一个患者说,这个病,网上不是说只活两三年,“怎么我到了第二年,我还没死啊?”
高红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说:“这只是概率,你会活得很长的。”
在这个公益组织做了两年,高红说,她也被患者的悲伤情绪感染了。一天,她突然手抓不住笔,吓得以为自己得了这种病。
中国医师协会、“融化渐冻的心”社会公益项目是2005年开始推广的,如今已登记了全国3000个患者的基本信息。办公室副主任黄敏说,浙江有100人。但她也说,这是保守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得的是这个病。
黄敏说,面对这种不能治愈、不知病因的怪病,更多的时候给人的是无力感,绝望后便是人与人的不信任。
以前黄敏也喜欢加入病友的聊天群,但是病友很反感黄敏建议的药物治疗,骂她是“卖药的”,她气不过,就退群了。
“在群里,任何推销药物的行为都是被人反感的。”群友李子告诉我,现在有种药物,一个月花费4700元,一年要近6万,但效果不佳,“一边吃药,一边看着自己身体力量的继续丢失,我凭什么要去相信卖药的人?”
不过在群里,推销药品,甚至声称气功治愈的大师层出不穷,有人抱有一丝希望,有人已经绝望,有人冷冷地看着。
张红是第三种人,她直接说,我不喜欢上QQ群,不讨论治疗。
黄敏也承认,目前世界上尚无治愈这种病的药品,但目前的药品可以延长人活着的时间。如果得病的身体情况像一个下坡的小球,那么药品就像挡板,可以减缓小球下降的速度。
“只能减缓,不能逆转。” 最后黄敏说。
其实可以这样活
今年,黄敏去了日本,参观了日本渐冻人协会。她说,日本渐冻人协会会长给她多年的志愿工作思路打开了一扇窗。
“其实渐冻人可以这样生活。”黄敏说,那个叫桥本的会长,气管已经被切开,有3个护工轮流护理,每天她靠着眼神和护工交流。
桥本每天的生活是,逛街、听音乐会、看电视,然后跟议员们讨论如何为渐冻人群体争取权益。
在中国,渐冻人药物目前是不在医保之内的,而在日本,类似药物全部报销,护工费用也是全部报销的。
“很多年前,日本和中国其实是一样的,”黄敏说,现在的一切都是桥本和日本渐冻人协会不断去努力争取来的。
一次,黄敏问桥本:“你怎么争取权益的?”
桥本说:“我这样了都这么坚强活下去,议员还能对我说不吗?”
这句话对黄敏触动很大。“只有靠不断地争取,才有看到希望的那一天。”黄敏说。
如何让小猫不冻着?
2010年10月20日,上午8点,陈霜的“渐冻人”聊天群显示,很多渐冻人起床了,群的对话总是从一个叫“画仙”的网友发送的一个“微笑”表情开始的。
“画仙”第一时间向病友们报告自己头一天的病情:今天脚有点萎缩,一点都不灵活。
病友家属“志”立刻提醒:你病情发展得太快了,这样下去明天可能就无法吞咽了。
第二天中午,“画仙”平静地告诉群友,吃的东西全部从嘴角流出来,她已经无法正常进食了。
随后她略带兴奋地告诉群友,家里的小猫生了一窝小崽儿,一团团粉嫩的肉,被包在铺满棉絮的纸箱里。
“眼睛都睁不开就知道咪咪地叫,我一整天都在想着怎么不让它们冻着。”于是,群友们纷纷出主意,为几个不曾谋面的小生命如何取暖出谋划策。
此刻,群里没有抱怨和哭诉,因为出现了一窝需要呵护的小猫。
记者手记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生命被冰封,我会怎么办?
去西藏寻访隐士,或者提早结束生命……
想了很久,我也没想好自己应该干啥。
在西安采访张红的时候,张红80岁的妈妈在厨房做饭。突然老人转身说:“我真希望这饭一直做下去。”
我知道,做饭意味着,张红还能靠咽喉肌肉继续维持吞咽功能。
但有一天,她要被切开食管,输入营养液。也有一天,她肺部肌肉萎缩,头脑清晰地迎接身体力量最后的消失。
这太残酷。老人说:“我真的受不了。”
房间内屋,张红的爸爸和保姆看着张红从小到大的照片集锦,一幕一幕,从婴儿到风华正茂,再到无力得像襁褓中的婴儿。
生命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轮回,令人唏嘘。
保姆三妹看着照片对我说:“她以前去过很多地方,她有能力啊。”
但艳羡后,三妹说,她想找个人,接替自己照顾张红。她说自己年龄大了,现在每天上午7点起来,晚上12点帮张红洗澡,吃不消。“有时候喂她吃饭,我睡着了,都找不到嘴的位置。”
“有一天你会走么?”我问。
“走了,这两个老人咋办?路都走不动了,每天还要去买菜。”午休时,三妹喜欢碎碎叨叨地给自己找离开的理由。不过三妹没走,朴质的道德观让她继续留下来。
他人的力量让生命尽可能有尊严地延继,明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死亡。
人类就是这样,友情、亲情、爱情的接力,让生命从一个绵长的夜晚过渡到第二天美丽的阳光。
把爱给予别人的幸福,足以让这个家庭充满前行的温暖,就算无力的张红,也在努力给予爱,这不能不看做人类精神财富的一种转移。
小区门外,一群人围着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老人裸着胸肌,张大了嘴巴,脖筋暴突地大声练嗓子:“依呀呀……”
厚重的秦腔洞穿了北方寒冷的秋夜。
境界,让死亡充满韵味;死亡,让人生归于纯净。
——张红博客签名
谈论生死,会不会残酷又显矫情?
看完张红的故事,或许你会有这样一个假设,倘若自己也不幸成了“渐冻人”,会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余生,迎接最后的暮鼓晨钟?
若嫌司马迁老人家“人固有一死”太老套,那不妨换个时髦的比喻,“人生好比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
该来的,终究会来。
现在的张红就像海滩边的一堆沙粒,每次海浪打来就被带走一点。
就这么意识清晰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渐渐冰封,先是手脚,再舌头,直至吞咽困难,呼吸衰竭。
有人说,她靠希望而活。但对张红来讲,不治之症带来的是满眼绝望。
医生断言,她活不过三年。
而张红就这么扛过来了,几乎丧失全部行动能力的她,还“笔耕不辍”,每天800字。
最近她张罗着开网店搞募捐,为条件差的ALS患者募集延续生命的呼吸机。
同学开玩笑,怎么比生病前事还多。
是张红天生坚强?
不。
她也有过恐惧,绝望,直到最后的淡然。
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你会为何而生?我问。
为爱。为亲情、友情、爱情,这三个亘古不变的真谛。张红用鼠标艰难地点出这句话。
张红博客里这么写着,躺在沙发上不能动弹的深夜,我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命和80岁高龄的父母紧紧相连。活着,好好地活着,是我的责任。
记得《肖申克的救赎》里Red有句经典台词,get busy living or get busy dying;汲汲于生,汲汲于死。
其实,我们总在忙,忙着追逐名利,忙着柴米油盐,忙着飞速奔跑,以至于都没认真想过,到底为何而活,为何出发。
采访结束,临走前一天陪张红的父母去买菜,看见小区门前贴着一张讣告。
张妈妈说,每当小区里有人离去,都会贴出来。说完,老人色黯淡了。
回到单位,QQ弹出张红的留言, “我觉得你的比喻很好,当潮汐带走最后一粒沙子时,人们偶尔会想起,这里还有过一堆沙子。”
敬畏生命,珍惜眼前,毕竟这里有我们的曾经。
特派记者 贾代腾飞摄影报道
- 2010-10-26中国20万“渐冻人”:目睹自己死亡全过程(图)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