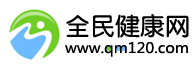性开放到底带来了什么
http://www.qm120.com2008-11-11 17:07:47 来源:全民健康网
10年前,当我们谈到“性”这个字眼时,估计所有人都会带着惊讶的表情,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
但10年后,当性革命袭来时,当“遮羞布”被扯下时,中国人心中压抑已久的便如洪水猛兽般迸发开来,“”、“”……这些以前提都不敢提的字眼似乎成了社会的高频词。
最近一组调查显示,上海市的婚前比率为69.34%;在北京妇产医院做中期引产手术的女性半数未婚,其中20岁以下的女孩占14%。同时,26.7%的男人一生拥有10个以上的性伴侣。
性问题上的这些变化,是倒退还是进步?中国的性现状到底怎样?未来的性将何去何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著名性学家李银河和中国性学会常务副秘书长薛福林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专访时,对“性开放”做了一番解读。
中国的性革命仅相当于美国五六十年代
《生命时报》: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性现状到底处于哪个阶段?我们现在开始性革命了吗?
李银河:中国的性革命是从30年前开始的。目前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只相当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现在人们更多强调的,除了性愉悦外,还有性权利,这是不小的进步。
《生命时报》:与美国相比,我们究竟落后在哪些方面?
李银河:主要还是法律。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很少,也不够科学。近十几年以来,我调查的一些数据说明,中国性革命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性观念也日益开放。比如1989年,北京的婚前只有15%,而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已经上升到了60%―70%;再比如,以木子美为代表的“”,在20年前是要判刑的,但现在就不会。
薛福林:我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不在“开放”与否,而在于文化。比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是握手,美国人见面打招呼是拥抱,你说这是因为他们性观念更开放吗?其实这是文化特色决定的。我看过外国的、性用品商店,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人如潮水。中国人的性观念的确有些落后,但在某些沿海地区,可是“开放”得很。
婚外性、是必然产物
《生命时报》:随着性观念的日益开放,对于派生出来的诸如婚外性、等一系列问题,您二位怎么看?
李银河:我把分成三类:一类是有罪的,比如;一类是有错的,比如婚外性;还有一类是无罪无错的。我认为,婚外性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法律不能干涉。而且,对于一些婚姻来说,婚外性的确是一种补足。比方说,一个丈夫60多岁,丧失性能力了;而他的妻子只有40多岁,这时就需要用婚外性来补足。还有大量的夫妻家庭地位不平等,丈夫总欺负妻子,这时,第三者就有其一定的功能了。
薛福林:对于婚外性关系,我的观点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礼”。我们在婚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于是对其他异性产生了感情,甚至性冲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本性。但这种冲动比较好不要化为行动,因为人毕竟和一般动物不同,我们的行动要受到法律、道德、文化的约束。
《生命时报》:李教授,您认为婚外性为什么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李银河:婚外是人的权利,法律没有理由干涉。在一些西方国家,40%的人有婚外性,法律怎么制裁?
但因为它是在有婚约的前提下出现的,而在婚约中,两个人许诺要彼此忠诚,如果一方背叛,肯定是不应该的。所以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
《生命时报》:那么,薛教授是否同意李银河教授所说的,婚外性关系不受法律追究,但要接受道德谴责呢?
薛福林:婚外性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外情”,它首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说它“不应受法律追究”或“人有进行婚外的权利”,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怀疑。你可以认为你有权利,但没有哪个法律授予你这个权利。因为一夫一妻制下的婚姻和性关系都具有排他性。如果你的“”伤害了你的家庭,那你的行为合乎哪个法律权利呢?如果你真想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先解除你现在的婚姻关系再说。
当性与婚姻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东西,要牵扯到很多事情――夫妻感情、家庭、金钱、脸面、其他人的权益,不是凭自己认为有“权利”就可以随便来的。
至于道德谴责,这个太理论化了。有些婚外性关系,家里人根本不知道,谁来谴责?让社会大众和媒体来谴责?中国人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谁愿意把这事搞得人尽皆知?至于说自我谴责,那些真正有责任心、不小心出轨的,的确可以做到,甚至后悔一辈子。可是这样的人现在有多少呢?加强教育未必能做到人人都有责任心。
《生命时报》:李教授,您提到,60%―70%的人都发生过婚前,其中也包括一些在校大学生。对于在校大学生,学校该持什么态度?
李银河:大学生年满18岁了,他们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学校可以以性教育、规劝为主。如告诉他们这样会影响学业、会怀孕,告诉他们如何预防性病。不久前,四川一所学校开除了两个发生的学生,这样就很不对。
《生命时报》:前段时间,哈尔滨相关部门指导性工作者用安全套,这是不是对的默认?
李银河:不算默认,只能说是防止艾滋病的一个很尴尬的手段。因为我们目前的法律是不利于控制艾滋病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其实这个事已经是不可逆的了,怎么扫也扫不完,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是利益驱动了。
薛福林:恩格斯说过,、是对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这话我认为很有道理。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婚姻的基础应该是爱情,但现实中,很多婚姻不是出于爱情,有些原来有爱情后来没有了。但出于我前面提到的种种理由,没有爱情基础,很多婚姻还要维持下去,那有了性需求怎么办?只得各自去外面解决问题。还有些特殊人群问题,如远离家乡的民工。但要说到该不该合法,那又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了。
《生命时报》:对于性工作者,您认为该用什么方法进行管制呢?
李银河:去年有个女人大代表提出过建立“”的提案,没被通过。在我看来,“拉”比“打”好。把她拽出来游街示众,用吓唬的方式解决不是好办法。而如果可以对她们进行一些技术培训,让她们有机会找到其他工作,肯定比单纯打击要好得多。
性教育还是重头
《生命时报》:那么,中国人现在性观念的整个趋势是什么样的?
李银河:应该说正在走出中世纪的阴影,人们的性观念比以前开放多了,起码不再认为性是件很龌龊的事。当然,一些不科学的法律也是有名无实,不再认真执行了(在西方叫blue law),这些慢慢也就消亡了。
《生命时报》:您不止一次地提到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的内容,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法律适用于性领域呢?
李银河:压抑越小越好。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说过,没有一个权力愿意放开性资源。那我们只能希望它对性的管理尽可能少些。要管理,但绝对不能太压抑。
《生命时报》:既然我们的性发展落后于美国,那他们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又有什么地方需要规避呢?一些落后的性观念通过呼吁能改变吗?
李银河:中国的性革命生不逢时,人们带着性解放初期的冲动,刚迈开步子,偏偏出现了艾滋病,让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但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比美国容易得多。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是“以性为罪”的,而我国只是“以性为耻”。
如果说经验的话,应该还是性教育。我国的性教育太落后了,对于性安全知之甚少。在北欧一些国家,95%―99%的人都发生婚前,可他们就能做到让100%的少女避免怀孕。相比之下,中国差得太远了。
薛福林:想用呼吁改善人们的性观念实在很难。因为观念的改变需要条件和时间,工作也应该是潜移默化,而不是在强力的宣传下促成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你根本不可能让百姓的观念超越经济基础。目前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性教育上,尤其是在校大学生的性教育。